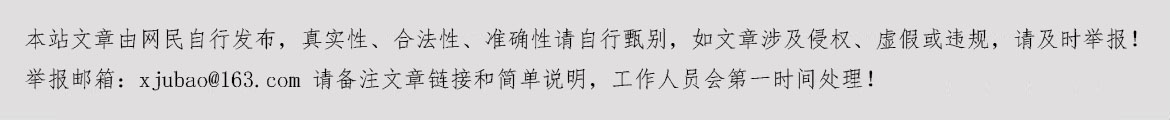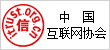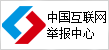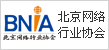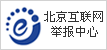当年,我是这样当兵到西藏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2022-12-18 10:12:14
我去当兵王心明
1968年12月,我初中毕业,回乡务农。那年我16岁。
从1969年春到1970年底期间,我先后三次报名当兵,热情满怀地去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挑选,可都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当兵无望。
三次报名皆落空
1969春季征兵工作开始不久,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
公路上,县革命委员会征兵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征兵宣传内容和军旅歌曲;路边的土壁上,随处可见用石灰水书写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大字体标语。
在那人人喜欢军用品、向往参加解放军的大环境下,为了履行兵役义务和减轻家庭负担,我和心纯大哥找到大队民兵连长魏大华报名当兵。
那时当兵,适龄青年要先在大队民兵连长处报名,然后到公社参加目测、初检;初检合格者,再到区里体检。
魏大华家住我们生产队的桂花湾,是1958年入伍的老兵,曾在部队当过司号员。他在参加四川甘孜境内的平叛剿匪中,身体受凉,因高原战区条件艰苦而未得到及时医治,导致声音沙哑。
我同心纯大哥参加了公社目测、初检。到参加区里体检时,没有我俩的名字。
1969冬季征兵开始后,我同心纯大哥仍然去报名参军。报名后,我们专门步行5公里乡间小路,到公社找到接兵部队干部,向他们表决心,坚决要求去当兵。接兵部队干部详细询问、并记录了我们的基本情况,叫我们回家听通知,做好“一颗红心,两个准备”。
我们顺利通过公社目测,到区里参加体检。大哥体检合格。我各个条件都符合体检标准,唯独体重差1公斤。
可是,这次征兵,我俩还是没有被批准入伍。
1970年冬季征兵,我俩仍然满怀信心去报名当兵,可最终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经过三次报名当兵无果,我心中有种失落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失落感不断增强。
1971年5月下旬,我在赶场途中,碰见小学同班同学、初中邻班校友、家住广田公社的陈代富。他已经当了两年兵,退伍回家了。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感慨颇多:同班同学陈代富当兵后都退伍了,可我还没有去当成兵,还在为没能去当兵而苦恼!
如愿以偿去当兵
转眼到1972年10月初,冬季征兵工作又开始了。
那天下午,我、心纯大哥和心愉弟弟正同生产队的社员们在地里干活,民兵连长魏大华找到我们,动员我们报名参军。
我们三弟兄都报了名。大哥21岁,我20岁,弟弟18岁。
对于这次报名当兵,我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能当兵更好,不能当兵,就在家务农也可以——我已经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了,队里常见的农活基本上都能应对。
我们在公社目测、初检时,认识了接兵部队到我们公社接兵的排长武克让、卫生员胡志才。
我们参加了目测、初检和区里正式体检,并顺利通过体检——高原兵合格。
生产队的社员见我们三弟兄都体检合格,纷纷议论道:按照解放前抓壮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惯例,这次你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要去当兵。
没几天,民兵连长魏大华通知我们:公社确定的政审人员名单中,只有我;大哥和三弟无望。
10月底,接连下了几天的小雨,小路泥泞,出行困难。
11月1日起,我们周边几个生产队的社员集中到本大队13生产队的岩湾子开会,听大队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
11月2日上午,在大队会计陈光荣的陪同下,接兵部队卫生员胡志才到我家政审、走访。
那天,我同生产队的全体社员正在岩湾子听大队干部传达中央文件。接到通知后,我和父亲冒着细雨,踩着泥泞小路,急急忙忙从岩湾子赶回家中。胡志才、陈光荣正等着我。
胡志才仔细询问了我和家庭的有关情况、征求了父母亲的意见后,叫我做好两手准备,听候通知。陈光荣帮我填写了一张油印的《应征青年情况登记表》(草表)。
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都没有我当兵的消息。
12月7日下午3点过钟,我忽然听见有人在屋外叫我的名字。我循声望去,看见从县城下乡到本大队的知青、与我同时报名的应征青年叶戌初、聂国辉,正站在屋外空地上,叫我去拿《入伍通知书》。叶戌初、聂国辉还通知我8日上午到公社换新军装。
我捧着《入伍通知书》,既惊喜又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看起来,这次当兵是板凳上钉钉子——稳当了。
我当即端了一张八仙桌的长板凳到屋后竹林空坝(那里清静),趴在长板凳上,写下日记:“72.12.7,星期四,阴。今天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我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从此,我便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到部队后,我一定听从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在部队苦练杀敌本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而战斗……”
12月8日,我同本大队的叶戌初、聂国辉、曾兴发、陈学明5名新兵来到公社换新军装。
在武克让排长指挥下,我们整齐列队,领取服装。每名新兵都领到了栽绒帽、罩衣(裤)、绒衣(裤)、棉衣(裤)、衬衣(裤)、袜子、白布床单、大头皮鞋、挎包、搪瓷口盅、背包绳、包袱皮等军用物资。
接兵营长杨炳刚、连长成海舟等人也到新兵服装发放现场督促、指导。
我们换好新军装后,在排长武克让等接兵干部指导下,反复练习打背包。我把领到的所有物资折叠好(小件物品用包袱皮包好),打在背包内,努力按军人的要求,做到捆好背包的背面,小背包绳“三压二”,即横向三道绳子压住纵向的两道绳子。
随后,全体新兵集合,听武克让排长讲解有关注意事项和要求。
武克让排长拿着一个与《毛主席语录》本差不多大小、封面印有“工作笔记”、“中国人民解放军〇〇七五部队”字样的红色塑料外壳的小本子,给我们讲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讲了人民解放军从“八一”南昌起义创建开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成长壮大的历史。他要求我们每一个新兵都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他还要求我们在离开家乡前,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做几件有纪念意义的事,如种一棵纪念树、为困难群众做好事等等。
12月9日,我抽空时间为本生产队的五保户、贫困户陈远亮家挑水。我先用竹竿把水桶放到深井里,等水桶装满水后再提上井口;两桶水装满后,挑150米远到他家,直到把他家水缸灌满为止。然后,我在桂花湾屋后的坡地上,种下了三棵桉树苗,作为当兵纪念。
12月10日,我同家人,并邀请清平伯父、大队团支部书记刘光友等,步行8公里,来到县城,找了一家照相技术好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合影照。
按照公社的安排,12月11日下午,全体新兵到公社集中,前往部队。我背上背包来到了公社。当晚住公社的木楼。我们打开背包,将被子铺在木质楼板上睡觉。
这时,我接到公社团委通知,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2月12日上午,我们全体新兵从公社步行到区里,再坐大厢敞篷卡车到县委党校,参加下午全县新兵向接兵部队交兵。
当年全县共征集6批新兵,我们这批新兵是第5批。这次武克让、胡志才到我们公社接新兵56名。
当晚,我们从县委党校步行到县川剧团,观看县革委会宣传队慰问新兵的专场文艺演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歌舞《洗衣歌》。
12月13日晚饭后,我们从县委党校步行到火车站。
14日凌晨,我同战友们一起踏上了北行的军列,开启了我人生中的军人之旅(直到1998年8月转业地方工作时才脱下心爱的军装)。
至于部队驻在哪里,我当时可不敢随便打听。在我的心目中,那毕竟是军事秘密。
军列到达成都后,我们下车换乘“解放”牌大卡车向西开进。
新兵车队经过9天的艰难行进,翻越了二郎山、折多山、东达山等几座大山,跨过了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等江河,行程1300多公里,在12月23日下午安全达到部队驻地——海拔4334米的西藏昌都邦达。
我在日记中记下了:“12.23,星期六,晴。今天下午,我们安全地到达了部队,从此后,我要在部队好好工作,听从上级的分配,真正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贡献”(不难看出,我那时的日记中,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痕迹)。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在部队各级首长的教育、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不断端正入伍动机,克服了部队驻地高寒缺氧、气候恶劣、条件艰苦等困难,安心高原,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积极参加国防施工、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王心明:四川省隆昌市人;1972年12月入伍,历任战士、司号员、文书、书记、副政治指导员、干事、参谋、科长等职;1998年7月转业地方工作,2012年9月退休。
作者:王心明
莫斯科世界杯 http://www.wuhefdc.com/3Ecl5/00642.html